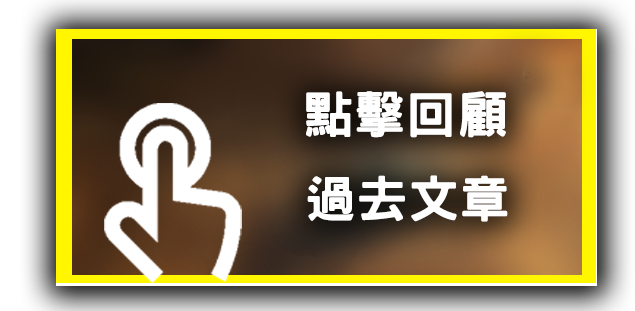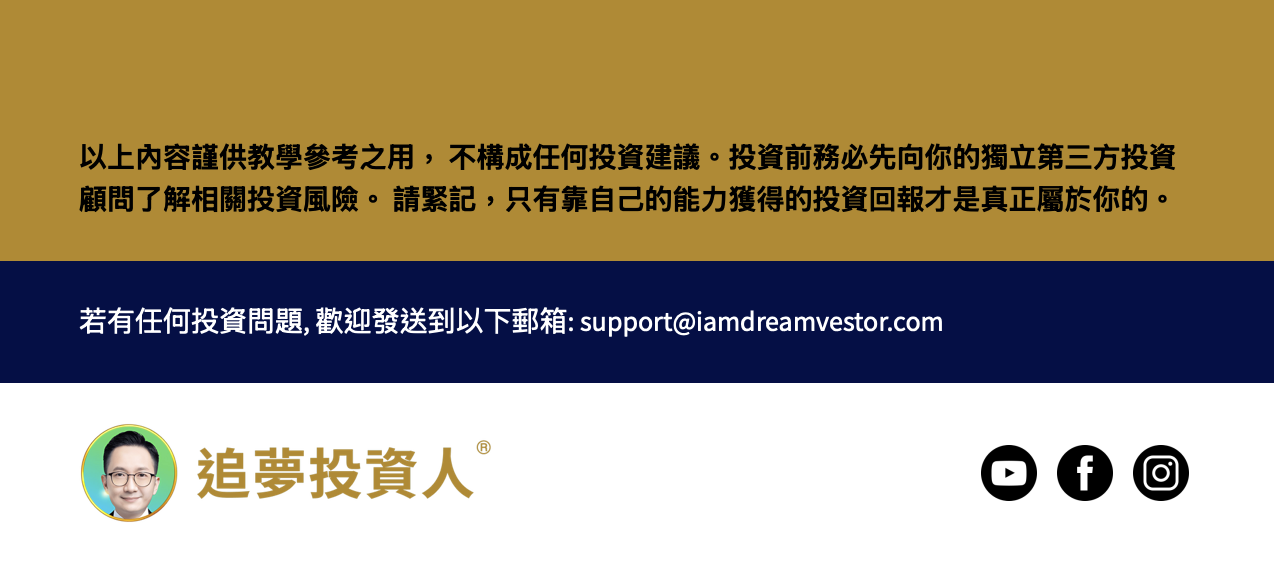標普500 🤫劍指10,000點
16.05.2025


【5分鐘閱讀】
最近打開財經新聞,充斥著對美國經濟和美股的悲觀預測!大家都在謾罵特朗普大規模加徵關稅如何搞亂市場,企業為了避開新關稅瘋狂囤貨,結果提前進口暴增,而消費者卻不敢花錢,導致2025年首季美國GDP年率下滑0.3%。這是三年來首次萎縮,淨出口對GDP的拖累更是創下自1947年以來最慘紀錄!更別提關稅戰帶來的成本上升和供應鏈中斷,企業和消費者信心直線下滑,商業信心指標跌到谷底,經濟活動放緩的陰影籠罩每一個角落。
更糟糕的是,政策不確定性和國際關係的惡化讓人無所適從;貿易戰疏遠了傳統盟友,國際合作受阻,有人甚至直言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減弱。這樣的局勢,難怪市場一片看淡,投資者膽戰心驚,彷彿美股又即將崩盤,長線上升不再,美國經濟也將一蹶不振!
然而,「在特朗普第二屆任期內,標普500 劍指10,000」 - 我認為很大機會會實現,這與我在2025年4月29日發表的文章「美股將創新高 🚀小心科技陷阱?」的觀點一致,也與我在過去4年在文章中一直認為美股中長線破新高一脈相承。
或許你會質疑:這怎麼可能?現在經濟數據如此糟糕,關稅戰打得如火如荼,衰退風險高得驚人,企業信心低迷,政策混亂不堪,標普500怎麼可能衝到10,000點?難道這不是痴人說夢?
詳細分析,請繼續觀看Pro 版

【15分鐘閱讀】
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0年),標普500指數的表現可謂一場驚心動魄的過山車之旅,但整體趨勢卻是穩步上揚的。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時,標普500指數僅為2200點左右,隨後一年市場迎來“蜜月期”,在減稅政策和監管放寬的雙重利好推動下,股市如火箭般飆升,至2018年初衝至2900點,升了三成。然而,好景不長,特朗普與中國的關稅戰(關稅戰1.0)如同一盆冷水澆滅了市場的熱情,美國經濟同步放緩,市場信心遭受重挫。2018年底,標普500指數暴跌約24%,回落至2300點附近,投資者人心惶惶。

⬆️2017年1月特朗普第45屆美國總統宣誓的情況
2018年底,在阿根廷G20峰會期間,習近平與特朗普會晤,中美達成90天休戰協議。美國允許對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只徵收10%的關稅,市場迅速重拾信心,標普500指數強勢反彈至2020年初的3400點,大漲50%並創下新高。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襲,全球經濟幾近停滯,美股在短短一個月內崩跌35%,指數重挫至2200點附近,又回到起步點。然而,聯邦政府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刺激政策與聯儲局的低利率支持成為救命稻草,市場以驚人速度反彈,至2020年底特朗普任期結束時,標普500指數已攀升至3800點,大漲70%,再次創下新高。

⬆️2017-2021年1月特朗普第1次就任美國總統4年間美股回報達80%
整個任期內,連同股息,標普500總回報約達+80%,年化回報率達15.9%,堪稱亮眼。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即使面對劇烈波動與不確定性,美國股市的韌性與政策支持往往能創造奇跡。
特朗普發揮資本主義到極致 - 巨大優勢
特朗普以商人身份治理美國的獨特模式,無疑為資本主義與國家治理的互動邏輯帶來了革命性的重塑。
相較於傳統政治家囿於意識形態與制度慣性的框架,特朗普將商業利益與國家戰略深度綁定,展現出一種「資本至上」的治理哲學。這一模式直指資本主義的本質——通過市場機制與利益驅動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從歷史數據與政策成效來看,這種商人治國的模式在多個領域展現出超越傳統政治治理的顯著優勢,為標普500指數劍指10,000的長期趨勢提供了強大支撐。
商業邏輯驅動的政策效率
首先,特朗普將企業經營的「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引入國家治理,極大地提升了政策執行效率。美國自建國以來,總統多由律師、軍人或職業政客擔任,其決策往往受制於政治妥協與繁瑣的官僚程序。
特朗普作為首位純粹商人背景的總統,將國家視為一間巨型企業,將經濟指標等同於國家發展的關鍵標尺。2017年,他果斷將企業稅率從35%下調至21%,直接推動標普500成分股企業淨利潤率從9.2%躍升至11.5%,在其首個任期內帶動該指數上漲80%。減稅政策宣布當日,指數創下當時歷史新高,資本市場的即時反饋印證了這一商業邏輯的成功。這種以結果為導向、快速試錯的企業家思維,打破了傳統政治的低效慣性,為美國經濟注入了強勁活力,也為股市長期牛市奠定了基礎。

⬆️美國歷任總統合照
資本賦權與監管鬆綁
其次,特朗普通過資本賦權與監管鬆綁,釋放了市場的巨大潛能。相較於奧巴馬時期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強化金融監管,特朗普政府大刀闊斧地廢除該法案核心條款,將華爾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降低15%,釋放超過5000億美元流動性,直接刺激了金融市場的活躍度。
另外,他更將矽谷「快速迭代、打破常規」的商業模式引入行政體系,例如任命馬斯克主導「政府效率部門」改革,旨在以企業化方式精簡官僚機構。
在科技領域,數據顯示,美國科技企業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從2016年的2.74%提升至2020年的3.07%,同期專利授權量增長18%。這種策略,讓資本在更自由的環境中流動與增值,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在全球技術與資本市場的領先地位,為標普500的長期上漲提供了結構性支撐。

⬆️ 2018年特朗普簽署通過金融改革法案,對美國資產規模較低的銀行放寬監管。
貿易戰的資本重組效應
再者,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雖短期引發市場震盪,卻在資本重組層面產生了深遠的積極效應。2018年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曾導致標普500指數短期下挫20%,引發廣泛爭議。
然而,從資本結構調整的視角看,這一政策迫使跨國企業加速供應鏈重組,進而促進了美國部分本土產業的復興。例如,蘋果公司將中國產能比例從47%降至2020年的35%,同時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0億美元建設數據中心,帶動當地半導體產業集群形成。這種「創造性破壞」雖帶來短期陣痛,卻使美國製造業回流規模在2017-2020年間累計達2500億美元。特朗普以關稅為杠杆,強行重塑全球資本流向,體現了商人「斷尾求生」的現實主義思維,也為美國經濟長期競爭力注入了新動力。

⬆️ 2020年初特朗普與中國簽署貿易協議情況
歷史不同模式對比
從歷史來看,特朗普的治理模式與傳統「大監管」形成鮮明對比,與羅斯福新政時期政府主導的經濟干預不同,特朗普通過關稅與補貼的組合拳,試圖逆轉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空心化。1950年代,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峰值達28%,此後持續下滑至2016年的11%,而特朗普任內將該比例穩定在12.5%。這種逆全球化策略雖違背戰後自由貿易傳統,卻契合資本在區域安全框架下尋求超額利潤的邏輯。類似1992年特朗普集團破產重整時,通過放棄49%股權換取5億美元債務減免的操作,其國家治理同樣體現了資本主義「以利益為先」的冷酷現實。
數據進一步佐證這一模式的資本效率:2018年稅改後首年,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匯回規模達7769億美元,是奧巴馬第二任期年均水平的3.2倍。這表明,特朗普將國家機器轉化為資本擴張工具的策略,雖加劇社會分化,卻在股市市值、企業盈利與技術創新等資本主義核心指標上創造了顯著短期紅利。
預期美股在未來的動力因素
儘管關稅議題的延長可能要等到七月初才告一段落,屆時市場或會短暫聚焦於相關討論,但過不了多久,投資者的目光將迅速轉向特朗普其他政策及其深遠影響。
政策延續與加碼:減稅、放鬆監管、基建刺激
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標普500指數飆升約80%,這並非偶然,而是得益於大規模減稅(企業稅率從35%降至21%)、放寬金融與能源監管,以及市場對基建投資的強烈預期。如今,特朗普已明確承諾將企業稅率進一步下調至15%(僅限美國本土生產),並針對AI與加密貨幣等新興產業推出減稅和激勵措施。這些政策可能直接推高企業盈利預期,提升估值,吸引更多資金流入美股。

⬆️ 美國能源部繼續放寬對能源開採的限制 (2025-5-11)
「美國優先」與貿易保護主義:短期利好本土產業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仍是高關稅與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歐盟、日本、台灣等經濟體全面加徵關稅,甚至推出「二級關稅」懲罰與目標國家貿易的第三方。雖然這可能短期推升通脹、加劇全球供應鏈波動,但對美國本土製造、能源、軍工、醫藥等行業卻是顯著利好。當市場預期「特朗普交易」延續,資金將加速輪動至這些受益板塊,帶動標普500整體表現。這種輪動效應,正是美股的推動力!

⬆️ 特朗普的支持者高舉美國優先的標語
市場信心與資金流入
作為商界出身的總統,特朗普深諳如何刺激企業盈利與市場氣氛。撇除關稅討論,他的言論與政策幾乎無一不對企業發展與盈利有利。一旦關稅議題淡出焦點,市場消息將傾向利好,資金回流股市的趨勢將更加明顯。這將為美股注入源源不絕的動能,投資者信心回暖,指數自然水漲船高。
比預期低的通脹:能源價格下行成關鍵
通脹作為市場關注焦點,其核心元素之一——石油價格,正受到特朗普政策的顯著影響。他一貫主張壓低能源成本,認為低油價對美國經濟、消費者與戰略安全至關重要。通過放寬國內能源生產監管、鼓勵頁岩油增產,特朗普正努力增加全球供應、壓低油價。在前天的聲明中,伊朗表態有意放棄核彈相關計劃以換取美國取消制裁。若美伊達成協議,伊朗石油重返市場將大幅增加全球供應量,對油價形成強大下行壓力。油價是通脹重要的組成部份,通脹若因此受控,美股將迎來更寬鬆的環境。

⬆️伊朗表態有意放棄提煉濃縮相關計劃以換取美國取消制裁(2025-5-15)
利率下行與併購活動活躍:額外動力不容忽視
即使關稅短期影響通脹,也僅屬過渡性質,因為關稅作為人為措施,隨時可由政府調整,影響完全可控。隨著能源價格持續回落,若通脹保持在合理範圍,聯儲局將有空間逐步減息,市場對此的預期將進一步為美股提供支撐。低利率環境不僅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還將刺激併購活動活躍,這些都將成為美股上漲的額外動力。
如何能加強投資回報?
縱使美國股票市場長線向上的趨勢無可置疑,正如我一直強調,這是資本主義核心機制的體現,但並非每位投資者都能從中受惠。
特別是那些以交易員心態進行投資的朋友,每當市場傳來壞消息,內心便充滿恐懼,忘卻了投資的初心,甚至被媒體影響,認為「這一次與過去不同」,於是在低位匆匆沽出;或者自以為能精準預測市場,打算在回落時離場再低位買入,結果卻錯失良機。相反,當市場飆升時,又突然想起美股長線向上的邏輯,於是傾盡全力在高位追入,結果往往是「左一巴右一巴」,投資回報不盡如人意。
投資者必須謹記,美股每年突然下跌8%是正常現象,甚至在周期轉換時回落20%至40%也在合理範圍內。若單純從頭持有到尾,根據歷史數據,美股平均年回報約為9%,而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更達到年均15%。
然而,若想進一步提升整體投資回報,關鍵在於找到適合自己,完全獨立於個人情緒的理性投資策略及工具,無論是技術分析(適合交易員)還是客觀的基本面分析皆可。
我個人過去十多二十年為客戶打造策略時,採用了對沖基金常用的投資周期學,通過簡單的周期計算,以特朗普執政周期為例,回報可提升80%至150%,同時整體波幅顯著降低,實現更高回報與更低風險的平衡。

⬆️與李嘉誠一樣,巴菲特一直進行價值投資到94歲退休,證明投資是適合任何人,直至到老;相反,我在投資銀行裏沒有見過交易員做大額金融交易是超過40歲的。
正如我在2025年4月29日及5月7日文章中所言,美股過去百年的表現堪稱「財富傳奇」。從2013年至2025年2月3日連續多年創新高,累計報酬率超過200%,年均回報達8-9%。儘管近期特朗普新政及關稅政策帶來市場不確定性與短期波動,但美國作為全球對資本最友好的市場,其中長線上漲趨勢仍是投資者可以共享的紅利。
作為中產投資者,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跟隨市場,獲得人人皆有的一般回報,更應通過系統性策略,力爭超越市場平均回報,穩健地獲得引以為傲的財富增值。
| * 以上圖片均來自互聯網的公開來源 |
|
|